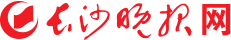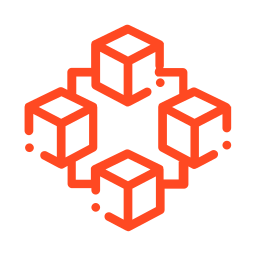散文 | 雨落老街
张镝
裹着渐次深浓的暮色,我们驱车六十里抵达老街,似乎就为赶这场雨。
街道依旧冷清,除了一家服饰店、两家杂货铺,老街再难觅到商业气息。很多门面空荡荡的,有的终日关着门,有的变成了居家的堂屋,还有的靠墙堆着散落的花炮筒子,等待勤劳的主妇们在闲暇时为它们糊裱纸。这条昔日繁华的主街落寞着,不断老去。
推开家门,只见一颗颗水珠沾附在地板上,密密匝匝,沿着墙角、地面,四处铺陈,从这头到那头,自门口至过道,直通最后的厨房,像被谁给捂出的汗滴。用拖把吸过,不久,另一层水珠漫上来,比刚才的更细密,像有一批撸不掉的小生命,生生不息。
有什么东西笼罩着全身,沿着肌理走向,粘连着皮肤。每个人都被罩住,推不开,也逃不出,像被装在一个封闭的口袋。
天地间像被谁挡住了,四处暗沉沉的。
一切表明,有谁在策划一场蓄势的等待,等待谁的隆重光临。
要下大雨了!有人站在门口,看着湿滑的地面,又抬头朝天空张望,喃喃出声。迷惘的眼神里,透出一丝不悲不喜的云淡风轻。
只有天井边的苔藓兀自绿着,保持着始终如一的静默,不惊不诧,似在轻吟浅语,我已低到尘埃,你们还能对我做甚?
天空有雨点洒下来,稀稀落落的,来得比较安静,连一个雷声也没有,闪电也看不见,驾着祥云,越过天际,扑至地面,算是开了张。一颗颗砸下来,有的落在瓦盖上,发出几声咚咚的闷响;有的扑进菜土里,留下“哧”的一声长叹,腾起一缕似有还无的灰,倏忽间不见;还有的带着无知无畏的勇气,想要给水泥路面一记响亮的耳光,“啪”的一下,犹如甩进煎锅的鸡蛋,由圆形或垂露形拍成一张薄饼,很快被地面吸干,无形消散。消散间,那豆大的雨点,润湿了点大的路面,使其颜色突然变深,纹路清晰起来,很快,就一点点淡去,直至全然不见,路面灰蒙蒙地恢复原状。这星星点点的雨和之前匍匐在瓷片上、玻璃上的绵密的水珠,敢情是暴雨派出的前哨,对这个世界所作的初期试探?
更多的雨铺天盖地而来,像谁发出了呐喊,战鼓铿锵,从天上包抄下来。雨点儿以排山倒海的气势,组成一支漫无边际的庞大队伍,黑压压地,朝大地风驰电掣般驰骋。呼啸间,带着力量,震得世界瑟瑟发抖。屋后的树木、蔬菜,如板栗、柚子,茄子、黄瓜,以及所有那些可以看得出形状的叶片,随着这雨点,周身剧烈地抖动起来,不知是迎合式的嘹亮欢呼,还是痛苦的低声叫喊,一致朝下,簌簌着跳起舞来。那些细小的枝条,像击打乐器,随着前后左右不同方位的敲打,以及叶片带来的震颤,跳跃式地摆动起来。只有树干安然矗立。几乎是纹丝不动的树干,似乎更能代表那棵树的本身,或是主心骨,表达着某种凛然接受的坚定。“任你东西南北风,我自岿然不动。”诚然,这里的风要代换为雨。
瓦屋上,叭叭嗒嗒的响声,越来越急,越来越密,最后所有的声音汇聚成片,响声大作。至于哪颗重些,笔直坠落,落在檐头,哪颗轻些,飘忽着飞到瓦棱边,斜斜打将下来,哪颗又被风带了一下,闪着腰猫进了灰缝,完全听不出了,所有的雨点声搅和在一起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犹如千军万马在奔腾,喧闹,嘶鸣,却又带着朝前行进轰然作响的步调,谱出一曲宏大的交响,撼人心魄。
世界唯有雨声。
一股股水声哗然响起,似瀑布流动,带着飞流直下的气势,屋檐水动起来了。屋顶上,雨水淌进瓦槽里,你挨着我,我挤着你,很快把槽挤满了。这些不安分的精灵,马不停蹄,沿着槽子,顺流而下,在屋顶上划出一排排竖线式的格子,淌出一排排小溪,朝下行进。到了屋檐边,这才发现,前方无路,无遮无拦,于是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淌将下来,在空中画出一条条晶莹的抛物线,哗啦啦,那是它们抑制不住的欢鸣,将天空与大地连为一体。
地面的水涌动起来了。雨水沿着檐下沟槽,随着地势急速流动,从高往低,一路欢歌。这流水,是千百年前就开始的循环往复,驾轻就熟,还是初来乍到,充满新奇?大约两者都有,难以分明,彼此裹挟着,带着无坚不摧的汹涌气势和些许的泥沙,咚咚锵,浩浩荡荡,朝前奔流。
街道上,不时有小轿车、工具车驶过,像一艘艘轮船,在街面的河流里劈波斩浪。水浪雪白,一团团一簇簇,沿着车轮翻滚着,飞扬着,跳动着,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一时的光影和绚烂。车过了,街头恢复平静,斜密的雨丝随风吹动,翩翩摇摆,在水面显出细碎有致的凹痕,像谁的裙裾在沿街扫动,原来,雨真的有脚!
屋檐往沟渠,小溪归大河。河水一寸寸地涨起来了,带着浑浊的深黄,打着旋涡,不断前进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