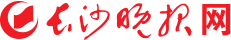韩少功何立伟带你回到文学烟花最美的现场

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
韩少功
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,会在寂静的山河间毫无踪迹
作为知青从长沙下放到汨罗后,韩少功就搞起了文学创作,因为《夜宿青江铺》被《人民文学》相中,被邀请到编辑部改稿子。“他就安静地坐在王朝垠办公桌旁的沙发上,下班跟着王朝垠回家,就住在王朝垠家里。”原《人民文学》编辑朱伟这样回忆道。
韩少功一直对《人民文学》编辑王朝垠心存感激,“我曾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,与他在北京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……”确实,从《夜宿青江铺》直到《爸爸爸》《女女女》,韩少功早期“三级跳”的作品,都是经王朝垠的手,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,并由此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
1977年恢复高考后,韩少功顺利地进入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,依然作品不断。“韩少功到北京来,我陪他去王府井,他已经在外文书店挑英文原版书了。我到长沙也去过他们学校,到他家里见过他母亲,他带我去橘子洲头、岳麓书院,现在回顾,还真有要‘到中流击水’的意气。”朱伟说。
大学期间,韩少功写了两篇极不一样的知青小说,一篇是《西望茅草地》,另一篇是《飞过蓝天》。《西望茅草地》写理想与现实的关系,讲述一个没有文化、不懂管理,却以理想主义感染着“我们”,表面朴素粗暴、实质亲切慈爱的老场长的故事。《飞过蓝天》对比着写一个知青与他心爱的信鸽。人叫“麻雀”,鸽子叫“晶晶”;人与鸽子建立了感情,但在关键时刻人出卖了鸽子,为一个招工名额将鸽子作为礼品。鸽子被带到远方,逃离后历经千辛万苦要回家,回到知青点的上空,却被人打了下来……这两篇作品,均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说到年轻时候的创作,韩少功记忆最深刻的还是知青生活,“夏天看荷花,冬天看梅花。大时代出大作家,小时代出小作家。知青经历对于作家来说也许算得上大时代。毕竟,了解底层、深入实际永远是作家的必修课。”
大学毕业后,韩少功留在了长沙。然而,那段贴近土地的知青生活一直是他的创作原乡。《爸爸爸》鸡头寨里痴呆的丙崽是他曾经可怜可叹的邻居,《马桥词典》马桥村里的乡土符号是他曾经耳濡目染的语言,《日夜书》里的大军、小安子、郭又军是他曾经日夜相伴的朋友。当然,他对土地不是没有逃离的渴望。在漫长的知青岁月里,和所有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,在血色夕阳里,“我们争相立下大誓,将来一定要狠狠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儿包子,要一口气看五场电影,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狠狠走八个来回。未来的好事太多,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。”
不过,正如他上世纪80年代振臂一呼的《文学的“根”》,“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里的文学之根”很快把他召回泥泞的土地。2000年,韩少功再度重返曾经的下乡地湖南汨罗,这一次是定居。新世纪之初,韩少功的隐居一度成为城市的话题,也令乡村的人们不解。但很快,种蔬菜挑粪桶穿解放鞋的作家韩少功成了汨罗村民口中的“韩爹”。晴耕雨读的生活浸润笔尖,酿出了诗意而醇厚的《山南水北》。
关于重返乡村的理由,韩少功写得诗意,“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,记忆或忘却,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,就会在寂静的山河间毫无踪迹。”告别了喧嚣的城市、浮躁的文坛、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,韩少功坦承,“我只愿意在这里行走如影子,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。”近20年来,韩少功和妻子一直过着半年乡村半年城市的生活。他很满足于这种状态,“人永远是矛盾的,向往自然也向往文明,都是很真实的心态。我希望找到一种平衡。”

何立伟
我对一切新鲜的事情葆有孩子般的兴味,于是童心泱泱
“在那边,白皙的少年看见了两只水鸟。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,在绿生生的水草边,轻轻梳理那晃眼耀目的羽毛。美丽。安详。而且自由自在……” 这诗化的语言,极具诗意的场景,叫人们怎么也忘不了这篇“短小精悍”的小说《白色鸟》和其作者何立伟。
《白色鸟》获评1984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汪曾祺形容何立伟“那时的文字有唐人绝句的影子,解人之言”。其时“伤痕文学”兴起,很多文学作品通过苦难的岁月、悲惨的事件的详尽描写,展示时代苦难悲剧的场景,以引起阅读者的心灵震颤,唯独《白色鸟》避开苦难的阴影,将镜头对准两位少年。小说没有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,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,作者有意淡化了小说的情节,使其更像是一篇诗意浓郁的散文,如诗如画,耐人寻味。
时隔30年多年后,何立伟谈起《白色鸟》的创作,依然憧憬着小说中所展示的画面:“小说里写的一些画面在湘江或者浏阳河边会经常出现,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大都生活得比较单纯,虽然生活在城市,却是大自然的孩子。”
顽童、绅士、匪气,这些似乎很难纠合在一起的词,却奇迹般地集结在何立伟的身上。对此,何立伟还乐意人们这样评价他,“起码真实”。文学、绘画、摄影,虽然没有宏大叙事,却结实、硬朗、有质感,一切皆娓娓道来、美妙呈现。早已年过花甲,被人称为像钻石一样拥有多个切割面的何立伟,其超然脱俗的风度,依旧如同“大自然的孩子”。
人们发现,何立伟不但会写,而且还很会“玩”。后来,何立伟还特别热衷于画画,但他却说:“我不晓得要如何认真地画画,就像写作一样,认真只怕也画不好,反倒喜欢漫不经意地涂鸦。”何立伟的文和画都有一股神韵。问他神韵怎么来的,他说没有刻意去想神韵,“艺术就是要有一股天真气,我喜欢拙,不喜欢巧。我的文学作品和画都是自然的,我就只能写、画得这么傻,傻乎乎的。好的艺术家晚年的作品都有天真气,只有经历了所有的巧之后,才能回到一种天真。”
何立伟的这种天真,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。“我喜欢过悠闲、懒散、不拘束的生活,我不喜欢别人管我,我也不喜欢管别人,我就喜欢做我自己,做自己喜欢的事,包括写写画画,很愉快的。我对一切新鲜的事情葆有孩子般的兴味,于是童心泱泱。”
何立伟有一股长沙“老口子”好玩的灵泛劲,但又透着阅历磨出来的练达通透,往往寥寥数笔,通过文字和绘画,让人玩味。人们几乎看不到何立伟“勤奋”认真的一面,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绘画作品,却又总是源源不断,“我以为写书读书如同做人,断不可太功利。凭着兴味来读书写书,似乎于我更相契。所以我读的书、写的书都很杂、很乱,然而于我的人生却大有裨益。”
何立伟所说或许就是“功夫在诗外”。俗话说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何立伟乐在其中。“前不久去丽江,我就远离随同的人,一个人跑到山顶客栈,叫上一杯茶,鸟瞰全城后,就从袋子里摸出书,一口气读完了一半。随后,又叫了饭餐,边吃边回味书里的妙处,这快乐别人哪里知道?丽江客栈有书吧,后院里有花草,太阳亮堂,找把竹椅躺下来,将书举得高高。读倦了,将书盖在眼上,囫囵睡一觉,蝴蝶在身旁绕来绕去,那个诗情画意呀,又有谁能体会其中的妙处?我这腿,勤快,不听使唤,喜欢各处走动。我这眼,喜欢看不同的世界、不同的人生。听不同的口音,望不同的面孔。这就是沈从文公说的,读社会这本大书,最难读,亦是最有益。而我的那些作品,也就是在那样不经意中写出来的,包括《白色鸟》。”
谈创作
文学的萤火虫之光依然需要坚守;敞开心扉写出来的东西,更能深入人的心灵
有人说,韩少功是最接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当代作家。对此评价,韩少功调侃道:“往好处说是多才多艺,往坏处说是不专业。但这都是令我感到快乐的东西。”
在《进步的回退》中,韩少功写道:“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,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。”他说:“技术的进步是阶梯式的,但人的精神和思想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,有时候甚至是回退的。”从文化寻根到现代性批判,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也经历着“进步的回退”。谈及作家如何应对复杂的媒介变化,韩少功道:“作家一是要顺变,要适应变化;二要守恒,不能随波逐流。”
前些年,商业浪潮、文学式微,韩少功对此并非没有认知。但对于他视作神圣的文学,他有自己的坚守和希冀,“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,需要持守,需要旁若无人,需要繁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。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‘小时代’正成为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……那又怎么样?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: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,萤火虫也能发光,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,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,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。要相信总有人会看到,即使是非常幽暗的光。”他鼓励当下坚持写作的年轻人,“要志向大大的,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淘汰出去。”
和何立伟在写作之余画画类似,韩少功写作之余潜心翻译工作,早年,韩少功就翻译了米兰·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。韩少功认为,文学创作与翻译互生互长:“翻译也是一种阅读,是一种精读。它会迫使你把书读得有深度,这对于强化我们的阅读能力是好事。”但近几年韩少功却又暂缓译笔,谈及原因,他自谦地说:“搞翻译我是捡遗漏。如今翻译家太多,不用我操闲心了。”尽管把翻译调侃为“闲心”,但韩少功仍旧爱之真切:“我希望有志向的翻译家,不要求快,要慢一点,精一点。如果光求快,甚至为了追求市场利润,匆匆忙忙,这对翻译的损害很大。”
韩少功自己也把握着慢而精的节奏,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,他淡然一笑:“计划不好说。计划了十条,如果只完成了两条,八条就算吹牛了。所以,等我做完了再跟你说吧!”
去年5月,韩少功和何立伟同台做了一次文学讲演。何立伟说,改革开放后,文学开始在文艺界蓬勃发展,文学潮流此起彼伏,流派消长更别。“那个时候,伤痕文学、知青文学、寻根文学、文学小说和文学实验小说等派别的代表人物和作品,湖南作家群体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中青年作家身上,如韩少功、残雪、孙建忠、彭见明等作家,《芙蓉镇》《那人那山那狗》《白色鸟》《爸爸爸》等作品也引起了广泛关注。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,现在就像烟花绚烂后又恢复了平静。”
何立伟坦陈,他喜欢短篇小说创作,跟他本人的爱好有关,“我是非常倾向于抓住生活中的某一点来进行开掘,从某种意义上说能让人更容易记住,能产生共鸣。言语无法抵达的,作品往往能直入人的内心,通过作品达到令人敞开心扉与人内心真正意义上的交流。短篇小说情节往往比较单纯,挖掘生活中某一个点,揭示人性,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在社会节奏如此快的当下,大把的时间被工作、生活等占用,短篇小说就更能适合当代现状。同时,当下也是适合创作短篇小说的最好时期。”
何立伟的思维总是像湘江水一样,是流动的,跟他谈文学创作,他会说画画;跟他说画画,他又会说读书。“随着科技的发展、社会的变化、人的生存压力加大,大量的工作时间被占据,阅读的空间被挤压,上下班期间的公交车上、地铁上,一天可能要浪费两三个小时,那么手机、平板电脑这种媒介就给了人们更多的读书选择,这里面有更多可选择的书可以读。当下,微信、微博就很好地适应了人们这一阅读习惯,也为我等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平台。”
“但是,凡事有利有弊,这种短平快的阅读,逼着人们变得肤浅,因为没有完整的阅读时间,没有完整的阅读,只是看到只言片语的小段子、小网文、微文章,其思想含量是非常低的,就如西方的肯德基一样,虽然好吃,但是没有‘营养’。”何立伟说。
文学创作是基于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上的,其作品就是一个时代缩影,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何立伟表示,相对于顺境,往往逆境中的经历对生活、对社会的感悟更透彻,也使人更冷静、更清晰地去洞察社会、洞察生活,“这种敞开心扉写出来的东西,更能深入人的心灵”。
>>我要举报